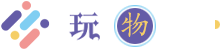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抗生素
65年前,大卫·利弗莫尔的奶奶在做完阑尾手术后撒手人寰。让老人去世的并不是手术本身,而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感染,因为在那个青霉素出现之前的年代,人们对感染束手无策。让我们回到现在,抗生素的时代正在走向尽头。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内,发明出来对抗感染的灵丹妙药,正在对细菌的战争中正节节败退。科学家们曾预言,传染病将绝迹于天下;而现在,后抗生素时代启示录正在向我们招手。

链球致热菌(Streptococcus pyrogens)照片由阿尔斯特大学盖蒂图片社的S·洛瑞提供
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夸张?很遗憾这不是危言耸听。医学杂志《柳叶刀之传染病》刊登了一篇文章,抛出了耐多药物性细菌正迅速蔓延的问题。我们面临这样的疑问,“这是否意味着抗生素时代的结束?”
虽然医生和科学家并非毫不知情,但蒂姆·沃尔什教授和同事通过他们的文章把把问题描绘的更为严重。2009年9月,沃尔什发表了有关一种新发现的名为NDM-1基因的文章,该基因可以在包括大肠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在内的不同类型肠杆菌间轻松穿梭,并使细菌能够抵抗几乎所有最新的强力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而《柳叶刀之传染病》的文章显示NDM-1广泛分布在印度,并且由于全球旅行、医疗旅游以及器官移植、孕期保健和整容手术等的普及,已经在英国发现其踪迹。
沃尔什教授说到,“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可能都预示着抗生素的末路。对能产生NDM-1的肠杆菌,现代医药中还没有行之有效的抗生素。人类可能还有大概10年的好日子,其间我们要非常理智地使用抗生素,但同时也要对抗那些无法治疗的感染。”
这还是乐观的看法——前提是制药公司能够并且愿意继续发明新的抗生素对抗致病细菌。上个世纪90年代,制药业在该领域的研发进入一个死胡同,在那之后,他们对麻烦的抗生素研究一直没有太多的兴趣。而且,抗生素只需要服药一个星期,而不像心脏药物那样终生服用,所以研发抗生素赚不到多少钱,同时随着病菌耐药性的产生也意味这个药物不再有效。
开篇提到的利弗莫尔博士现在是英国健康保护署(HPA)抗生素耐药性监测和参考实验室的主任。去年HPA向医疗从业人员发出有关NDM-1的警告,敦促上报所有疑似病例。利弗莫尔对未来毫不乐观。
他说,“如果我们无法治疗感染,很多现代医学将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以移植手术为例,其中必须抑制患者的免疫系统来让肌体接受一个新的器官,但这样就会使病人容易被病菌感染,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使用免疫抑制剂治疗癌症上。
但这不仅仅是尖端医药的问题,抗生素对腹部手术也是关键。“你要防止细菌流窜进入病人的体腔内,如果你无法治疗这些感染,就会有更多人死于腹膜炎。”阑尾手术也会变得异常凶险,就像1928年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之前那样。
当然那还不是世界末日,他说“我们肯定能搜肠刮肚地找到对抗某些细菌感染的抗生素。”
无药可用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当有人发生严重的感染——比如血液中毒——造成高烧,医院的医生会把血液样本送到实验室化验,知晓是何种感染。但这需要时间。利弗莫尔说,“在接下来的48小时内,医生会给您使用抗生素,用来对抗感染。因此在这48小时内,并不知道治疗是否起效。致病菌的耐药性越强,抗生素起效的可能性越小。”
他说,研究表明如果致病菌是耐药性的话,死于肺炎或败血症(血液中毒)的可能性会高一倍;如果是细菌耐药性肺炎的情况,死亡概率会从20-30%上升到40-60%。
迄今为止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医生们都清楚的知道他们在与细菌感染比赛,不过与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相比人类总是道高一尺。但10年前出现的所谓超级病菌MRSA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医院出现感染耐甲氧西林(迄今最强效的抗生素)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病人。由前政府首席医务官利亚姆·唐纳森领导的对MRSA和艰难梭菌(Clostridium difficile)的全面战争减轻了革兰氏阳性菌对病患的威胁。医院在卫生状况也做出大量改进,以部分回应市民的忧虑,而制药公司也在寻找对抗感染的抗生素上投入重金。

沙眼衣原体(Chlamydia trachomatis)照片由眼科学/科学图片库提供
但这就像用手指去堵大坝上的孔洞,到头来只会发现洪水从别处涌出。细菌是伟大的幸存者。专家认为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耐多药性革兰氏阴性菌(如产生NDM-1的肠杆菌)以及一种名为KPC的酶,它会导致细菌对(曾经)最为强力的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产生耐药性,而这种酶已经在美国(在以色列和希腊)传播。
“抗生素耐药性的出现是对达尔文进化论最有力的佐证,”利弗莫尔说。“这是一场消耗战,认定人类会取胜是一个天真的想法。”
现在的策略是控制这些细菌的传播。卫生清洁具有明显的作用。更好的清洁、洗手液和对工作人员与市民的严辞警告都有助于降低医院感染率。但是,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医疗相关感染中心主任理查德·詹姆斯教授警告说,耐药性致病菌不会只留在医院里(实际上,产生NDM-1的细菌通过受污染的水在印度社会广泛流传,而居民在这种受污染的水中洗澡、洗衣服和排泄)。
詹姆斯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生物流入社会。有必要进行关于感染的公众教育,例如做饭时应注意厨房卫生。我这一辈人被灌输很多卫生的观念,每顿饭前要洗手,这已经成了个人习惯。但是很多这些习惯已经不再提倡了。”他说,在学校中采取创新的想法来教导孩子要洗手——希望这些孩子回家后也要求他们的父母做同样的事情。
除此之外,真正需要对现有的抗生素进行保护。“在我看来,它与全球经济的能源问题有许多相似之处,”他说。人们试图通过碳交易来节约石油并减少其污染物的影响。一些有意思的文章建议征收对抗生素的庇古税——意在对导致环境问题的机构征税,以作为一种缓解问题的激励措施。
他指出,抗生素的效力如同石油资源一样是有限的,而耐药性的花费并没有反映在药物的价格上。“如果你认为抗生素效力是像石油一样的资源,你想通过增加税收来保持其效力,”他说。这将是全球范围内的,而该收益可以为新药研发提供支持。
但应当对救命的药物收税么,特别在贫穷国家中?詹姆斯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什么都不做,以后也不会有任何抗生素。至少这是一个可行的建议。”
如果有人还在考虑,沃尔什的文章显示不论是英国还是别的国家,都不可能如此而为之。哈罗盖特地区医院的微生物学家顾问凯文·科尔说:“这份报告显示,如果想通过正当使用抗生素来应对耐药性超级病菌的出现,这必须各国统一行动。”英国伯明翰大学分子遗传学教授克里斯托弗·托马斯说,“这需要将健康问题作为世界问题来考虑,在地球某处的医生使用抗生素的方式可以迅速对其他地区产生影响。”
“坦率地说,制药公司以及各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需要真正地共同行动,”沃尔什说。他一直协调努力在全球建立良好的监督系统,以监控耐药性产生的种类和地点,并随之进行干预。在哥伦比亚、墨西哥、泰国和印度,他都获得了支持,愿意参与监测计划,但欧盟委员会却不提供资助。“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每年3万欧元,这并不是很多钱。”
事实是,许多人还在采取鸵鸟政策视而不见。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NHS医院不能根治病患的感染。在这场人类与细菌之间你死我活的战斗中,最好情况大概也就是一个平局——如果我们够幸运的话。
后抗生素时代:当抗生素不起作用时,会发生什么?
· 移植手术变得几乎不可能。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必须终身服用免疫抑制药物,以阻止对新器官(比如心脏或肾脏)的排斥反应。如果没有抗生素,他们的免疫系统就无法对抗威胁生命的感染。
· 切除穿孔的阑尾又会变成一种危险的手术。手术后,通常会给病人注射抗生素以防止可能的细菌感染。如果细菌进入血液,它们会引起败血症而危及生命。
· 肺炎再一次成为“老年人的朋友”。肺炎曾经是一大生命杀手,尤其对年老体弱者,肺炎会让病人陷入昏迷而在睡梦中故去。正是抗生素从肺炎的手中挽救了许多生命,从而其他诸如癌症之类的老年病才成为健康克星。
· 淋病将变得极难治疗。耐药菌株正在增加。如果不治疗性传播疾病,会导致盆腔炎、不孕症和宫外孕。
· 结核病将成为不治之症——最初是结核病,后来是耐多药性结核病(MDR-TB),现在又有了极端耐药性结核病(XDR-TB)。结核病治疗需要很长的抗生素疗程(6个月或以上)。停止服用或忘记服食(非常人性化的倾向)已导致耐药性的扩散。
抗生素耐药性——超级病菌来袭
1945年12月11日,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在颁奖演说的最后他给后人发出一个警告。一种名为青霉菌的霉菌对弗莱明培养的细菌具有抑制能力,他的这一偶然发现启发了两名在牛津工作的研究人员,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和恩斯特·钱恩(Ernst Chain,1945年诺奖的共同得主)提取了青霉菌中抑菌的主要活性成分,将其变成现在广为人知的灵丹妙药——青霉素。但在当时,弗莱明已经预见到抗生素滥用的后果。他说,“如果没有科学常识,人们很容易吃药吃得不够,这样会将微生物置于非致命性的药物剂量之下,使其产生耐药性,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做法。”
青霉素及受其发现所推进的其他抗生素的发明,与疫苗接种是医学中最伟大的两项发明。然而,弗莱明的警告一直困扰着医学界。如今,抗生素的耐药性已经变成一个花销巨大和危及生命的问题。有人担心可能会出现更糟的情况,比如耐药性细菌的某个菌株就可能引发无法治疗的疾病流行。虽然有了弗莱明的警告,人们也对耐药性的产生机制和针对措施有了充分的认识,但是如何实实在在的解决这一问题却还没有定论。贪图方便、懒惰、不当的财政激励措施和纯粹的坏运气,使得各种防范耐药性的努力都化成泡影。
有理由相信由耐药性细菌引发的疾病大流行永远不会出现,至少在常规使用抗生素的过去65年中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即便耐药性这一问题还不严重,它也在不断给医学界制造麻烦,引发疾病、占用经费,而这种境况在经济困难的国家尤为常见。
不可避免的病菌耐药性
贪图方便和懒惰是抗生素耐药性的最主要成因。这是因为错误使用这些药物的人,大多数都不会直接承受其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抗生素可以对抗细菌,但对病毒无效,但患了病毒性感冒或流感的病人总是要求医生给他们开抗生素处方,而这种自我放纵的行为几乎不会给自身带来任何危害。而为了摆脱多心的患者,开出无用处方的医生也不会受到惩罚。但是,这些因为疑心病开出来的抗生素,却可以成为耐药性细菌产生的温床,并且可能传染给其他人。即使正确开药,那些不能服用整个疗程药物的人也难咎其责。在世界某些地区,甚至不需要开处方就可以拿到抗生素。不需要诊断,也没有用药建议,在柜台上就可以买到多种抗生素,这进一步增加了滋生耐药性病菌的人体反应容器的数量。
这一问题还不仅仅局限于人类。美国国会议员路易斯·斯劳特尔是一位微生物学家,她分析了官方报告,计算出全美五分之四的抗生素是给牲畜使用,并且常常只是为了促进生长就给完全健康的动物注射抗生素。这种做法便于降低肉价,但却为病菌创造了更多产生耐药性的机会。
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因为抗生素耐药性会导致医疗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双方面浪费。它会导致更长时间、更为严重的疾病,延长患者的住院时间,复杂化其治疗方案。其中,某些病人的死亡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研究人员在一项对芝加哥库克县医院近1400名患者的研究中发现,在188例细菌耐药菌株感染的患者中,有12人因得不到适当治疗而死亡。目前,耐药性细菌主要威胁儿童、老年人、癌症患者和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但是,以后的情况可能会更糟。每年,都会新增近45万例多重耐药性结核病的记录,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死于这种疾病。最近在俄罗斯部分地区确诊的结核病新增病例中,其中四分之一以上由这种棘手的耐药菌导致。
而药物价格也过于高昂。非营利性组织“慎用抗生素联盟”基于库克县研究计算出,仅美国一年在抗生素耐药性上的花销就在170亿至260亿美元之间,大概占全国医疗保健支出中的1%。
不过,美国是富裕国家,能够负担得起这部分医疗开支。穷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抗生素的滥用使他们陷于不利境地。国家越穷,用于药物保健预算的比例越大。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去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抗生素耐药性通常会增加在药物上的花销,因为患者不得不放弃价格便宜、广泛使用的药物(正因为其广泛使用,才导致耐药菌株的进化),而服用更昂贵的替代药物。这给贫穷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例如,医院用于治疗一例多重耐药性结核病的费用,可以治疗200例普通结核病。
诉诸行动,不要惊慌
对于这种情况,有三种可能的应对措施。一种是什么也不做,给予药物更大的补贴,在可接受的成本范围内治疗耐药性病菌导致的各种疾病。这里有史为鉴。青霉素发明之前的1940年代中期,完全健康的人即使不小心划破了皮肤,也有可能死于败血症。其他许多细菌感染,特别是结核病,也都是常见的健康杀手。莎士比亚的诅咒,“愿瘟疫降临于你的房屋”,在那个时代会引起真正的共鸣。然而,抗生素和疫苗将那种境况变为历史。与过去每年数百万计的死亡人数相比,每年因结核病死亡的人数大概有150000,去担心它有点吹毛求疵。当然,如果这些患者没有死亡会更好。但限制抗生素的使用也会导致病人的死亡,特别是医生开处方又贵又费时的贫穷国家中,而用了药他们可能就活下来了。
耐药性的产生可能是自我受限的,这种想法有其基本生物学原因。对于致病菌,想要进化出耐药性是耗费巨大的。病菌必须改变其生理过程,因为耐药性常常通过制造蛋白酶来降解药物,或者制造出更多拷贝的转运蛋白把药物泵出细胞之外,这两方式都需要大量的能量。有些病菌看起来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至少对某些药物不可能。属于链球菌一个物种的化脓性链球菌从未产生过对青霉素的耐药性,而另一种肺炎链球菌却常常可以耐受这种药物(见图1)。在这种情况下,耐药性微生物从理论上来看并不像是一个超级病菌,而更像是娇生惯养的生物,只能在医院或诊所这些有利的擂台上打赢病人。这也是接受现状的另一个原因。
不幸的是,这种令人欣慰的说法未必全是对的。2007年,安特卫普大学的微生物学家赫尔曼·古森斯在《柳叶刀》杂志中展示了旨在探讨这一想法的试验结果。他的研究小组将健康的志愿者分成三组。给第一组志愿者名为阿奇霉素的抗生素。给第二组克拉霉素。给第三组安慰剂。随后记录了每个志愿者喉咙中链球菌的变化情况。
如其所料,在那些服用安慰剂的志愿者体内,在研究过程中都没有链球菌耐药菌株的迹象。而在那些服用抗生素的志愿者体内,链球菌耐药性在几天内急剧升高,这也符合预期。但令人惊讶的是,获得耐药性的链球菌菌群可以存活一年以上,这引起了大家的担忧,因为人们认为耐药性细菌只有在选择性压力存在的情况下,才具有相对于非耐药性细菌的优势。
不少人认为耐药性微生物在自然界不是优势生物,是因为这合乎进化的逻辑。但假如这是错的怎么办?因为即使大多数病菌都没有接触过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病菌只是非常小的比例,但是耐药性不论怎样都是一个问题。那么自然而然的下一个反应就是试图限制药物滥用。
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埃默里大学詹姆斯·休斯的文章,出版在今年二月份的《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文章显示多达50%的抗生素给药是不必要或不恰当的。过度使用、滥用、剂量不当、使用不合格或稀释药物,这些都有助于耐药性的产生。薄弱的卫生保健系统以及缺乏有效的监管也是原因所在。除非实施严格的规范禁止抗生素的滥用和有效的系统来监管医生的行为,否则他们完全可以听任治疗眼前病患的意愿,而不去担心理论上的十年后可能会承受抗生素滥用后果的病人。
限制抗生素滥用困难重重,需要政府、公司和卫生保健机构采取一致行动。甚至可能需要病人不要只想着自己。在贫穷国家免费分发药品的援助机构和慈善组织也应当检讨自己,是否能保证和教育患者正确使用强力药物,如果目前的做法不当,还可以做哪些改进。政府将财政补贴与药品发放相挂钩的做法必须废除。
监管机构需要在监控和公共卫生监督方面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使假药、不合格药(例如活性成分剂量低于标准)不会流入不知情的患者手中。也可以鼓励研发快速便携式诊断系统(这也是一个快速发展领域),当确认需要后才可以开出抗生素。
最后,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医生们要更加严格,而患者要接受抗生素不是万金油的观念。医学协会可以设定更为严格的培训和配药协议,例如让医生检查病人是否正确按疗程服用抗生素。
所述这些措施都是有利的,但大多数有悖于人类的天性。屠女士有另一项提案。她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项限制农业用途抗生素的法案。
愚昧的人类,聪明的微生物
还有第三种针对耐药性问题的对策。这就是生产新的抗生素,初期使用时细菌不会对其具有耐药性。很多人可能会感到惊讶,抗生素库里的许多最佳武器其实还是几十年前弗莱明和他同时代人所熟悉的老药。最后需要讨伐的两个原因是不当的财政激励措施和坏运气。
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的4月7日定为世界卫生日。跟所有行动日一样,世界卫生日也有一个口号。今年的主题是抗生素耐药性,而口号是“今天没有行动,明天没有治愈”。但在近年却鲜有相应的行动,或者说成功。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在1983至1987年间批准了16种新型抗生素。但2003年至今,只有7种抗生素获批(见图2)。而且,如果知道其中细节,你会觉得情况更加糟糕。比如制药公司在结核病药物领域已经持续多年没有巨大突破,虽然其中有些前景看好的药物。
关于这一问题有几个原因。其一是早期的研究人员运气好。正如现代制药业开始于阿司匹林的开发(从未被其他药物超越的药物),而青霉素及其同时代药物由于疗效显著而易于发现,这些药物并不容易进行改进。
其二是现代科学并没有为制药提供帮助,这个问题以前是没有人想到的。制药公司投入了巨额资金进行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研究(研究蛋白质如何行使功能),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结果寥寥。英国大型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的大卫·佩恩,在几年前的《自然》杂志中撰文道,尽管花费了数百万经费,各个公司还是两手空空。“显然想找到药物标靶是很困难的,我们只好停手了。”另外一些药物研究主管也经历过同样的挫折。瑞士诺华公司的马克·菲什曼说,由于在基因组学方面缺乏类似的突破,“我们已经用回到穷尽筛选的老路上,从能够杀灭有害菌的数百万候选药物中筛选和评估对人类安全的药物。”
有迹象表明大型制药公司的研发经费正在枯竭。今年二月,世界上最大的制药公司辉瑞公司宣布将大幅削减其研究预算。受影响的研究方案中包括该公司的抗生素项目。不过辉瑞公司坚称没有削减该项目,只是将其从西方实验室转移至中国。
倒霉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不过研发新型抗生素不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不可原谅的,虽说可以理解。制药行业的人虽然不会在公共场合下承认,但实际上对抗生素的投资并不能吸引制药公司的兴趣。如果不考虑耐药性,现有的药物还很有效。虽然耐药性感染非常严重,但由于耐药性感染只占总数的很小比例,所以其市场规模也不会太大。事实上,大多数耐药性问题都发在负担不起新型药物的贫困国家,这也进一步限制了研发投入。此外,使用抗生素的成功治疗即为治愈。重复开处方并不必要。这对病人是好事,对制药公司却不是。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抗生素的研究已完全被放弃了。与其他药物研发领域一样,现在正出现越来越多的地方小型生物技术公司,而不是传统的大型制药公司。例如,旧金山附近的Theravance公司最近开发出一种治疗皮肤感染的抗生素,其中包括应对MRSA(多抗生素耐药性金黄葡萄球菌)引起的感染。美国马萨诸塞州莱克辛顿的Cubist药厂也在研发另一种治疗MRSA的抗生素。他们所研究的达托霉素已经过测试,但被大型医药公司礼来公司拒绝了。公司的研究人员发现,该药物会引发肌肉损伤,建议停止其开发。但Cubist公司的研究人员找到了通过调整用药剂量来缓解副作用的方法。现在,达托霉素在市场上也获得了成功。
不过这样的成功只是个例,而不是常态。为了改变现状,美国传染病学会(IDSA)提出了“10X20”计划,旨在2020前研发出10种新型抗生素。IDSA提倡财政激励措施以鼓励抗生素研发上的投入,如税收抵免、市场保障和现金奖励。IDSA还提倡针对特别棘手疾病的新型药物应该得到额外的专利保护。
公众的悲剧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滥用抗生素的好处是针对个人的,而损失却是公众的。如果没有外部干预,这类问题几乎没有解决之道。普林斯顿大学的莱曼纳 莱克斯敏纳然耶多年来一直思考如何解决抗生素耐药性的问题,他建议应当采取萝卜加大棒的措施。针对新药与快速诊断系统的得当的奖励基金或采购保障,可以克服抗生素的经济问题,使其用于治愈而不是治疗。针对医生和药剂师的更为严格的配药指导方针,可能有助于解决过度治疗的道德风险。
不妨现实一点。牛津(洛里和钱恩曾在此工作)的微生物学顾问德里克·克鲁克观察到,“当抗生素是真正有效的时候,很难大规模限制其使用。在亚洲某个国家短期内大量使用抗生素可能是一个好事。”由于不知道引发耐药性所需要的抗生素的确切剂量,也使限制抗生素的使用备受争议。
牛津克鲁克博士的同事蒂姆·皮托对耐药性可能会带来一场灾难的想法持怀疑态度,他还指出许多现代手术依赖于低水平的感染风险。现在,这种风险接近于零。如果耐药性菌株的出现将这一风险提高到5%,甚至10%,大量的骨科手术、白内障替代手术以及其他酌情的但可以提高生活质量的手术停掉就可以了。届时虽然不是世界末日,但也是大步的倒退了。如果因为漠视弗莱明那么多年之前的警告,将这位先人留下的遗产挥霍而空,这将是全人类的遗憾。
Ainll-弦夕综合编辑整理![]()
以上内容信息以及包含的资源全部引用、摘录、转载自网络,图片、音频、视频存在无法获取/播放的可能性,因此资源可能已被源站删除或管理方下架。可自行关键字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