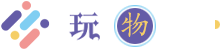香烟与乡土中国
近日看了魔鬼教官黄章晋写的文章《中国香烟的政治经济学》,为教官钩沉探幽的功夫折服,不由得想起了少年时在乡村见到的许多有关香烟的小故事。或许能从中一窥中国南方乡村社会的某些肌理。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坚定的控烟主义者。
去年11月,我参加中国控烟协会纪念“控烟十年”的一个会议,会上我谈到了自己对控烟的感受,对中国控烟的前景感到乐观。理由是,至少在我的生活中,相互不敬烟太正常了。作为一个不吸烟者,我家里从来不备香烟,也没有烟灰缸。无论谁来家里做客,奉茶之外,我从不会敬烟,偶尔有客人拿出自己的烟想抽,放眼客厅,找不到烟灰缸,于是作罢。
这当然是在北京,一个烟民到不吸烟的朋友家里做客,主人不敬烟他不会觉得受到了慢待。相反,在不抽烟的人家中吞云吐雾,烟民一般会觉得内疚。——哪怕主人一再申明:没事,你想抽就抽。
一旦离开北京回老家,情形就大不一样。从京城到省城,再到县城,最后回到生养我的那个小山村。越往下面走,“香烟文化”越浓厚。
恰好,就在我参加完“控烟十年”会议的几天后,我回到湖南老家,行程中所见证实了我上面的判断。
到了长沙,和几位老朋友相聚,有官员请吃饭。席间给每个人敬烟,敬的不再是一支,而是一盒软蓝芙蓉王。我摆摆手,说“谢了,我不抽烟。”对方也就不再将烟塞给我。回到县城,一位抽烟的朋友同行。在老家买卖做得好的一位高中同学请吃饭,开席前敬烟,依然是一人一包蓝芙蓉王,我照样推辞,老同学无论如何要让我收下。从长沙和我随行回家的那位朋友说,入乡随俗,老兄弟的烟,你就是不抽,得收下吧。
我知道这是他委婉地提醒我。我离乡多年了,没有意识到不接受老同学的烟,很可能会视为失礼。于是便把那包烟揣进兜里。
第二天回到距离县城30公里的老屋,父母很欣喜,还留在村里的族人——都是五十岁以上的长辈或兄长闻讯来家里探望。父亲嘱咐我发烟——他抽了五十年的烟,后来得了肺心病,2010年春天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后,便戒断了烟,因此家里也就不存烟了。
我知道,如果我不给同族的长辈和堂兄们敬烟,一定会被他们怪罪,认为我瞧不起他们。父母也会感觉到很没面子。幸好,那包老同学给的烟在兜里。于是拿出来扯开,一人敬两支。可是,我没有打火机,无法给他们点烟,这在乡下也算失礼。一位堂哥一笑,说,知道你不吃烟,不带打火机,没事,我这里有。于是他拿出火机打上火一一给点上,最后点燃自己嘴里那一支。
我在北京“控烟”的坚定性,到了老家,也就打了折扣。
香烟,是如何深入到我老家那个偏僻的山村的?我的祖先们,究竟是从哪一代开始抽烟的?
据史料记载,烟草在明末传入中国,到了清朝初期,抽烟成了贵族和官员中的时尚。朝鲜李朝《仁宗实录》丙戌(1646)五月条记载:“九王喜吸南草,又欲得良鹰,南草良鹰,并可送入。”九王即睿亲王多尔衮,朝鲜国王敬献烟草和良鹰以取悦这位执掌大清国柄的摄政王。由此可知产于美洲的烟草有一条路线是经过朝鲜从北面进入中华,烟草入中华的是另一条路线从福建、广东沿海登陆。香烟从高层的时尚行为“飞入寻常百姓家”,应该经过一段时间。那么,我猜测湘中农村的人抽烟的历史不会早于18世纪。但具体哪一朝,已难考证。反正从我记事起,村里只要是成年男人,就没几个不抽烟。——不抽烟的男人被人看不起,一般是“妻管严”。
祖父抽的是水烟,整个家族只有祖父和另外几个族祖父抽水烟。抽水烟的多是德高望重的长者,坐在太师椅上,左手端起白铜铸造、擦得铮亮的水烟壶,右手用一根麻杆引火,点燃烟斗里的烟丝, “咕噜”吸了一口,然后很享受地半闭着烟,背往椅子靠背上一仰。非常有范。或许是看过《神秘的大佛》的缘故,我心里总认为抽水烟的是地主恶霸之类,因为电影中的沙驼爷手拿着水烟壶。多数老农用旱烟管抽烟,我国“文革”时期老贫下中农的标准形象是对襟衣、布巾缠腰,腰上插一根旱烟管。我家有一根长度有些夸张的旱烟管,从烟嘴到烟斗的铁管有三尺长,是曾祖父传下来的,祖父用水烟筒,这传家宝便给了父亲。父亲也不用,于是常被我们兄弟拿来当棍棒飞舞。父亲告诉我们,这旱烟管就是曾祖父一件趁手的武器,平时用来抽烟,遇到袭击就用它御敌。
父亲那辈人已经很少用旱烟管或水烟筒了。在外面工作的抽纸烟——即商店里卖的,但多数不带过滤嘴。在乡务农的人则抽“喇叭筒”——用土纸把旱烟丝卷成喇叭形状。父亲在外面工作,但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在家务农,负担重,抽不起纸烟,又觉得用报纸卷“喇叭筒”太寒碜,不符合他一个公社卫生院院长的身份。于是他和许多家境不好的基层干部一样,买了一个手工卷烟机,用专门的白纸和烟丝,自己加工成两头一样粗的烟卷,看起来和商店里卖的纸烟没啥区别。
乡下人待客,有“烟酒茶饭”四端,其中“烟”排第一名符其实。乡间人际交往,只有对重要客人,才会请他喝酒、吃饭,或向其奉茶。而敬烟则是最宽泛的交际手段,第一次认识甚至是陌生人碰面,拉近彼此距离的方式就是敬烟。香烟,也成了物质匮乏时代,农民除了必须的煤油、布匹、盐巴、农具等商品外,购买量最大的一种商品。农家在逢年过节或贵客来时,才会到商店里买几把纸烟,一户人家待客的纸烟标准,基本上代表着这家的家境加大方程度。我记得少年时最便宜的香烟是7分钱一包的“支农”牌,稍微富裕的家庭则用2毛2一包的“岳麓山”待客,买2毛7钱一包的“香零山”的人家很少。小学毕业时,我们班同学为了感谢班主任——一位退伍的民办教师,小伙伴们问父母要钱,给老师买一包“岳麓山”香烟。以地方名胜为香烟品牌,似乎全国皆如此。当我成年后,第一次上岳麓山,马上想到的就是那个香烟品牌。
为什么贫穷的湘中农村,男性抽烟那么普遍呢?我想一个最大原因应该是当地种植烟叶。在人民公社时代,种烟叶是我们生产队最重要的一项副业,队里修建水利设施、买农药化肥或年底可怜的分红,主要依靠卖烟叶所得。生产队山坡上的旱地,几乎全种着烟叶。烟叶阔大,沾满露水,煞是好看。可牛从来不嚼食,而喜欢趁人不注意偷食禾苗或菜叶。长辈人告诉我们放牛娃的舌头也分得出好坏来,烟叶子太苦,它当然不吃。
我家屋后面,是生产队专门用来烤烟叶的烤房,尖顶,大烟囱。墙很厚,外面还涂着厚厚的黄泥巴。有一个大炉膛,一位在六十年代大饥饿时期从中专学校辍学回家的族叔,庄稼活不好,被队里派工专司铲煤烤烟。趁着露水未干,队里的农民将烟叶一片片采下来,挑回队部,一片片拴在木棍上,再搭在烤房里的架子上。然后封闭烤房,由司炉的族叔点火,往炉膛里加煤。一房子烟叶从青变绿,要好几天。烤烟火候最重要,火太小,烤不透,还发青,烟丝就烧不起来;烤过头了,烟叶发脆,烟味儿全没有了。因此烤烟的那几天,司炉者昼夜不得休息,隔一段时间要去查看火候,添加煤块。
烤烟的季节多在中秋节后,天气已经转凉。孩子们喜欢围着烤房的炉膛取暖,或者从收割完的黄豆地里捡来遗漏的豆子,交给司炉的族叔,让他放到空空的煤铲上,伸到炉膛里烤熟。
一房烤烟出炉,是生产队的大事,成年男子钻进温度还未完全降下来的烤房将烟叶取出来,老把式检查一番评定烤的质量,如果烤得恰恰到位,会说一句:这次烟叶能买个好价钱。于是围观者欢呼雀跃。
因为生产队产烟叶,一部分烤好的烟叶分给农户,队里男人抽的便是这样的自产烟。——当外面工作的人回村,向某位农民敬纸烟,被敬者谦让的理由便是:我吃的是队里烤好的毛烟,冲头大,吃你那个纸烟,不过瘾!说归说,他们一般会把纸烟接下来,然后夹在耳朵上面。乡村红白喜事后,酒醉饭饱的男人们回家,几乎人人在左右耳分别夹一支香烟。
1982年生产队分田到户,需要集体协作的烟叶种植和烘烤,也就无法进行。于是几年后,那座烤房被拆除了。
现在我回老家,几乎见不到农民种植烟叶,可是,农民抽烟和敬烟的陋俗并没有消失。打工的年轻人回家过年时孝敬长辈的必是一条条越来越高档的香烟。
中国的控烟,最难得不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也不是机关、学校、商店这样的公共场所,而是在我老家那样的乡村。
来源:十年砍柴
以上内容信息以及包含的资源全部引用、摘录、转载自网络,图片、音频、视频存在无法获取/播放的可能性,因此资源可能已被源站删除或管理方下架。可自行关键字寻找!